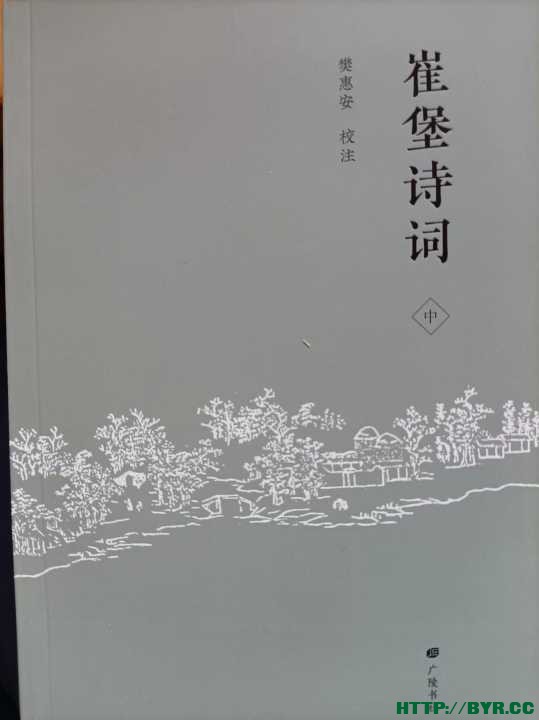关于人格底线的叩问(代序)
--李映华同志长篇小说《叩问》评读
韩 厉 观
《叩问》是一部正面写“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作品。主人公黎天明属于“老三届”,“回乡知青”;文革期间农村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作者凭借“个人记忆”,叙述了黎天明从学校的革命派到回乡知青,因父亲政历问题成为黑五类狗崽子,30岁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又参加全国统考,被高校录取。全画幅的展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起落,揭露与批判了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内乱”给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造成的破坏,特别是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所造成的难以弥补的精神伤痛。
不堪回首而回首,是历史的反思。毛主席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反思与总结。作者丝毫不隐晦自己的写作目的:就是提醒人们在生活一天比一天富裕的今天,千万不要忘记过去。“我把发生在家乡郭氏桥地区的诸多人和事串联起来,再现当时的社会,让读者和后人了解那段丧失理智的动荡历史,体味那个时代生活的艰辛与不易”。他怀着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警示后人要时时牢记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告诫握有话语权力者,不能重蹈覆辙。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精神。
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反思总结“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作品早已有之。有以刘心武、卢新华为代表的“伤痕文学”; 丛维熙、张贤亮的“大墙文学”;且因此有了谢晋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巴金的《随想录》,震惊当时的知识界;杨绛的《干校六记》引起众人的共鸣。出版较晚的《往事并不如烟》(章治和),揭示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历史隐秘。还有专写知识青年生活的《北大荒》等等作品。或小说、或电影、或纪实、或散文,无不以个人体验为文本主体,因此也都不可能对“文革”作出全面而公允的历史评价。
对于一个长达10年,涉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评价,原本不属于文学家的事,也不是任何一个个体案例所能概括的。迄今为止,对这一历史事件作出权威结论的是1981年6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文献,对于我们如何去认识理解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与危害极具指导意义,也应当是文艺工作者创作涉及“文革”题材的作品,如何贴近与体现主流精神价值体系的纲领。
把李映华同志的《叩问》,放在众多以“文革”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评读,一点也不雷同,且有鲜明的个性。集中到一点,那就是作者以一个生产队在10年“文革”中的大事记和一个回乡青年在10年“文革”中沉浮挣扎,提出一个无可奈何的问题:什么是人格的底线?须知,在“文革”中,“人格”、“道德”、“操守”这些概念都被打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烙印。作者偏偏就借黎天明之口,针对种种无法解释的现象,提出人格的叩问。这恰恰就击中了问题的要害,成为这部小说的闪光之处与价值所在。
《决议》这样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并一再指出,要把毛泽东的错误、党的错误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区分开来。不可忽略的在红卫兵运动和一系列“群众专政”活动中,特别是以革命激情掩饰的“群体暴力”活动中,固然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可乘之机”,也有不少好人干了不该干的坏事,这分明便是道德的缺失,人格的扫地。我们的党不可以把责任推给群众,作为身受心感的群众,面对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咄咄怪事,就不能不怀疑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人格的底线在哪里?如果我们的道德坚守多一点,这个历史悲剧恐怕很难拖那么长,危害那么惨烈!
也许正是这样的主题定位,作者的笔墨没有过多地用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上,而是以平直的叙事,娓娓诉说主人公黎天明的生活琐屑和在琐屑生活中承受不公正待遇之后的思考、追问。观其10年生活,找不到任何大公无私的英雄行为,也没有丝毫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中国共产党的不满与怨尤。对于无端的政治打击,他会辩白自己的无辜。除此而外,他一心只想凭借自己的才智和力量,为老婆孩子争取温饱的生活。每有所得,哪怕只是微乎其微,他会收获莫大的欣慰。这个形象,摆在文革中江青的文艺公堂上就是被重责的“中间人”的典型,是一定要批倒批臭的,这恰恰是大多数回乡青年的思想状况,甚至是大多数善良的老百姓的生活常态。正是在这种看似常态的生活中发出的询问,才是最深刻的。因为这种追问,不仅是在叩问别人,也在叩问作家自己。
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面对《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说,他近年来的进步就在于不再仅仅评判别人,而在评判别人的同时追问自己。这或许可以印证李映华小说的思想深度吧。《决议》中这么一个论断是非常中肯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
作者关于人格底线的叩问,还让我们油然想到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祝福》等。我们这个民族精神中许多落后的东西,譬如“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笑穷妒有”、“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等等。还有一个“耻辱观”的问题。在非常时期,人格扫地、尊严无存、恬不知耻,这是最让人心痛的。胡锦涛同志在他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特别提出“八荣八耻”,正是为了重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道德堤坝。因此,我们还应当这样来评读李映华的大作。他对人格底线的叩问,绝不仅仅为了总结过去三、四十年的历史经验,更是对现实的叩问。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应当怎样来坚守人格操守,这很重要。在法律荡然无存的“文革”中,道德是我们每个人尊严的最后的防线;在今天法律健全却“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情况下,道德操守应当是每个人管好自己最好的约束,这就是刘少奇同志在他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中所提倡的“慎独”。
以上所言,有点“主题先行”的味道,为新锐作家所不屑,其实“文以载道”、“主题先行”恰恰是为文的客观规律。就是福克纳、马尔克斯等魔幻大师,哪一部作品没有主题哩?不论怎样随心所欲的作品,总是作者心之所向意志所指的载体,只不过高明的作家把自己的主题思想隐藏得深一点,令人不易得而已。
说了作品的主题,再说作品艺术营造。看上去,作品按时间顺序,平铺直叙,即使如刑讯“同善社”、枪毙余百川也没有特别扣人心弦的场景,或渲染一个令人久久难忘的高潮,这恰恰是作者匠心之所在。试问,共和国主席都成了“叛徒、内奸、工贼”,拷打几个农民、枪毙一个不服改造的右派分子,值得大惊小怪吗?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让人精神疲劳了。对于黎天明来说,最要紧的还是挣工分、养家糊口最为现实。
小说安排了两条线,一条线是黎天明的生存生活线,一条线是周边发生的“米饼案件”、“新华党”,也就是阶级斗争的线。作者将黎天明的生活线作为主线,生存、发展是人的第一需要。阶级斗争这条线却若隐若现,时显时泯,穿插于主线之中。黎天明的生活看似正常,其实时时生活在政治的高压态势中,生存原本不易,犹如床底下的仙鹤,饭好吃、头难抬,这对于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日子何等难挨!
从在校的革命动力,一下子变成回乡知青尚且说得过去,由于父亲的历史可能有“自首叛变嫌疑”的揣测,自己一下子变成黑五类的狗崽子,这在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盛行的年代里,犹如跌落万丈深渊之中。“自立门户”之后,他一心想凭借自己的努力,做一个好丈夫和称职的父亲,然而办不到。父亲不光彩的政治历史,成为子女生存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妻子同样参加“开门红”,却和“五类分子”一样得不到表扬;自己拼命干活,评工分却被压在二等偏下。这不是少几分钱的事,是人格尊严的屈辱。转而借助家传的手艺私下做柳器贴补家用,也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堵死。拾粪、割草、打柴、上河工,把浑身解数全都使上,到年终决算,还“透支”56.3元,不是别人帮助,连口粮都称不回来,这就是那个岁月许多人的生活实录。全生产队农户靠200多亩土地来养活,本来就薄弱的生产力,时时还要受到“浮夸风”、“瞎指挥”的破坏。“平坟造地”、“塘粪垩田”、“推广红萍”、“扒苗助长”等等。因“透支”而称不到口粮的,绝非黎天明一户。在“文革”的政治高压下,人们敢怒而不敢言。
“米饼案件”是一个荒诞不经的传奇,然而却是当时的一宗“惊天大案”。神汉作法祛灾,要求病家放九九八十一撮米和(袋)饼。放完之时,就是病除之日。子女照办,才放几撮(袋)米饼,被人发现,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米,谐音,指美国;饼,形圆,喻苏修;越传越奇,层层上报,变成了特大政治案件,是时正好有美蒋飞机空投传单,佐证了内外呼应。省市县派员组成工作组,本地的干部群众参加排查,指鹿为马,把无辜农民抓来吊打,甚至采用火刑,蛇刑,最终不但逼出了投放米饼者,还挖出一个反动组织——“同善社”,说这是一个相当于“一贯道”的反动道会门组织。每揪一个人,不但要承认自己是“同善社”成员,还要交出十名成员,勾连罗织。黎天明的父亲、岳父都被打成同善社,友映公社加上周边的公社,竟然揪出261名“同善社”成员。有成员交代出某月某日“武装暴动”,武器已经运到,沉在大潼河。省里来的王组长,解放初期参加过平叛“腊八暴动”。以为真有故伎重演复辟颠覆的危险,到大潼河打捞武器,什么也没有捞到。“暴动”子虚乌有。方知“米饼”案件,原来是一出类似内部资料报道的《屁案惊动中南海》荒诞闹剧。于是通知放回所有被拘禁的农民,悄然撤出工作组。
如此近乎儿戏的阶级斗争,对农村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破坏,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吗?这不是任何具体执行者的过失与犯罪,这是在政治高压下,无政府主义“群体暴动”的恶果。夏二黑被活活打死,胡小英被逼死,颜同河、黄山被“披麻戴孝”折磨死,乃至于从无锡遣回乡劳动的大学生余百川,被其表弟揭发而送上断头台,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不足为怪。在这样的环境中,新生儿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一个生产队里同年生的五个孩子,不到一年死了三个。黎天明的女儿也因营养不良,差点窒息而死。他用自己珍藏的5元钱救治了女儿的小生命。
这些文字,读来让人泣下。更荒唐的是,民兵营长为了夺取大队长之职位,竟然撕毁大队长家的毛主席像,栽赃害人,虽得逞一时,到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生产队长为了强暴女社员,就抓住女社员丈夫是“同善社”,生死权掌控在自己手中,迫使其就范。还有公社革委会王主任的儿子在家里滥施暴力,使妻子张老师不堪忍受,以死抗争,谁知融化了大量安眠药片的水被醉酒的丈夫误食,差点被诬为谋害亲夫的杀人犯,最终因“陪枪毙”而成为精神病患者。“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阶级报复,好人光荣。”成了“群体暴力”对一切被打击个体实施侵凌的“理论依据”;“文攻武卫”,则是群体暴力对群体暴力的“最高指示”,最终连县革委会主任都被打死了。一切都超出黎天明的想象,他只能发出对人格底线的叩问,甚至陷入到“因果报应”的迷茫中。
对于黎天明来说,最可怕的不是父亲给他的政治包袱,而是害怕被人抓“现行”。终于有人检举他仇恨毛主席,在主席像的嘴上揿了图钉,聪明的父亲知道,这时辩白图钉的由来是不明智的,一口咬定是年幼的小女儿无意按在画像上的。法律没有了,道德伦理不存在了,良知也找不到了,只剩下这一点舐犊之情来为儿子构筑一把脆弱的保护伞。不过也恰恰是这份浓浓的亲情支撑着黎天明,鼓励他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在私下谈话中,父亲借古喻今,常用岳飞等忠烈故事鼓励他。妈妈和妻子在政治挑衅面前,坦然相向,决不后退。父亲和妹妹为了保护他,挂牌,批斗陪斗,在所不辞。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一面尽力帮助党支部写材料,刷标语,一面出去代课,解决经济上的困顿,也逐步走出自己的思想误区。
浊者自浊,清者自清。事实上,十年文革也并未使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的人格底线破碎不堪,不可收拾。作者一面通过主人公发出叩问,一面又通过小说中许多人物给出答案。虽然有王大兵、吴志良那样的“小人”无所不用其极,也有王富这个三代贫农出生的儿时朋友以身作盾,处处帮助,保护着黎天明。赤脚医生徐怀玉、南京知青舒梅英,都是坚守人格底线的艺术典型。大哥在安徽遭政治迫害能迅速澄清,还以清白。姐姐帮他找到代课的机会,让他从亲情、友情中看到了希望。林彪阴谋败露之后,尽管还有“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段被扭曲的历史,但距离“正本清源”已经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小说在黎天明考取大学结束,十分自然,他的叩问和答案全在这里了。
作者极力避免是非美丑一刀切,或“高大全”、“假大空”的艺术塑造,着墨无论多寡,字字落在实处,尽量保持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性。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可信的故事,塑造了一群平凡而值得品味的艺术形象。主人公黎天明的朴实、诚恳、勤奋、睿智、妥协甚至有点软弱,但不言弃的个性,更具说服力。
作者在书面语言上的造诣,非一日之功。学校的基础,社会的实践,特别是数十年高中语文教学的磨砺,使作者在汉语表达上准确、形象,拿捏到位。丰富的叙写中,幽默、蕴藉,温文尔雅,这种境界恐怕是一般人学不来的。我喜爱这样的文字。
作为小说,李映华同志还要多作一点推敲。如前所说,全面解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小说家的事。一部十几万字的作品,解说一个公社大队故事的文学作品,却千方百计要把文革的历史背景、运动过程、严重后果都一一交代,能承载得起吗?把历史学家、人文学者、马列主义理论家做的事都揽到自己的怀抱里,怎么忙得过来呢?主人公就一农村知识青年,那么重的担子,他挑得起来吗?幸好只是写主人公的迷茫、叩问与追求,尚落在实处。
作者宣称他的小说“七分真实,三分虚构”。这说明作者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理解失之偏差。小说的品格就在于虚构,小说家的才华就体现在想象与虚构之中。优秀小说的故事与人物都是真实的,这种“真实”不是事实有据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是典型意义的真实。
2014年4月20于宝应